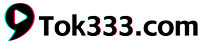责任编辑: q8ytop.com
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•斯蒂格利茨(Joseph E.Stiglitz)被誉为“集精湛的经济学家、机智的论辩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于一身”。近日,他受邀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主题讲座,和现场读者分享了他的新书《通往自由之路》(The Road to Freedom: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)。
斯蒂格利茨表示,《通往自由之路》这本书的名字从弗里德里希•哈耶克(Friedrich Hayek)1944年出版的著作《通往奴役之路》(The Road to Serfdom)中获得启发。不过,他和哈耶克的观点完全不同。斯蒂格利茨在讲座中首先解释了他所理解的自由。“近年来,在美国,自由的概念已被右翼甚至极右翼所掌控。共和党内提出让政府关门的委员会被称为‘自由党团’(Freedom Caucus)。要知道,这实际上会毁掉我们的体系,毁掉诸如退休福利或健康体系之类的东西。他们却将其称之为‘自由’ ……而我想做的,就是为进步人士重新找回自由的概念。自由就是发挥自己潜能的自由,过有意义生活的自由。这就是我想阐述的自由概念。”
斯蒂格利茨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这个概念。经济学家使用了“权衡”(trade offs)一词: 即你要得到一利,就有一弊。你要得到某种好处,就要付出某种成本 。斯蒂格利茨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
“一些人随身携带AK47自动步枪的自由意味着另一些人失去了生存的自由,这一点显而易见的。在美国,每天都会发生一起枪击案: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,甚至连报纸都不会报道。你必须杀死20人以上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。因此,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生存自由,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(Freedom from fear)。富兰克林•罗斯福(Franklin Roosevelt)曾谈到,四大自由是多么重要,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。现在在美国,每所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都要学习当持枪者闯入教室时该怎么办,而家长们则担心他们的孩子放学后会不会回家?因此,我们已经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。现在,我们需要权衡,你是否应该给每个人携带AK47自动步枪的自由?还是生存的自由、免于恐惧的自由?我认为,任何理性的讨论都会得出这样的观点,即携带AK47自动步枪的自由不如其他自由重要。”
“也可以用红绿灯来说明。在拥挤的城市里,红绿灯剥夺了你的自由,因为在它变绿之前你不能走。显然,这是一种约束。但如果没有红绿灯,在纽约的街头,没人能走。一个红绿灯,一个简单的规定,实际上给了每个人更多的自由。这也是一种隐喻。再举个例子,我们刚刚经历了新冠疫情,如果没有mRNA疫苗,我们也不会有今天。这些疫苗基本上都由政府买单。mRNA疫苗的研发费用也是由政府支付的。这意味着什么?如果政府要买单,就得有人纳税。税收就是一种约束。这种限制给每个人更多的自由,活下去的自由。纳税,可以扩大每个人的自由。这正是国家的一个重要作用。”
回顾历史,1929年持续到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后,经济学者们对大萧条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,提出了大量经济学理论,凯恩斯主义便是其一。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,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。受凯恩斯主义影响,二战后,许多国家,包括英国都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。在美国,杜鲁门总统也提出过全民医疗保险计划,但被美国医学会组织的反对呼声击败。如今,美国的医疗体系依然以商业保险为主导。
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弊端,他解释:“很明显,私营部门未能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。我们在美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。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%,而我们的医疗结果却比任何其它先进国家都要糟糕。”他希望政府能在维护基本社会福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“哈耶克可能会说,这是在为专制铺路,因为他认为这会导致专制主义。 70年后的今天,我们知道他大错特错了,我们看到的是‘专制民粹主义’(authoritarian populism)的盛行,比如出现了像博尔索纳罗(Jair Bolsonaro)和特朗普这样的人。你会在那些政府做得太少,而不是做得太多的国家看到更多类似的问题 。在北欧国家,民主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。”
米尔顿•弗里德曼(Milton Friedman)是上世纪中叶的重要的经济学家,他坚持经济自由,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。斯蒂格利茨表示和他很熟,但并不认同他的观点。“他写了一本书,叫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(Capitalism and Freedom)。这本书的主旨是,市场是有效率的,如果要实现民主政治,就需要‘自由市场’。所以,他说他想要自由市场,不仅是因为经济效率,还因为政治利益。直到现在,我一直认为他——虚伪,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仁慈的词。因为奥古斯托•皮诺切特(Augusto Pinochet)一接管智利政府,他就跑到智利出谋划策,利用皮诺切特把他激进的右翼思想、自由放任经济,强加给智利人。结果,他们用武力,而不是自由,不是民主,来让他的想法得到尝试,结果失败了。智利遭遇了近代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。他们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偿还债务,摆脱弗里德曼导致的困境。我想说的是,他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政治自由,任何致力于政治自由的人都不会以这种方式支持皮诺切特。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制造不平等,让垄断者和剥削者肆意妄为。后来,他和妻子罗斯•弗里德曼共同写了一本名为《自由选择》(Free to Choose)的书。在我的书中,我把他的书名改为《自由利用》(Free to Exploit)。他认为,不应该有反垄断法、竞争法等,市场本身总是充满竞争。环顾一下我们今天的处境,很显然他们错了。”
弗里德曼的理论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,并且对1980年代的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出:“我认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非常成功地推销了一种理念,即‘新自由主义’。他们说它是现代的,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。但实际上,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没有任何区别。这种思想非常强大,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都接受了这种思想。 市场力量会促使企业努力降低成本,生产人们想要的产品:这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想法。但他们忘了,有时通过欺诈、占人便宜和破坏环境,可以更好地增加利润。要知道,利润最大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福祉最大化 。”
“另一个问题是,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观点对某些人来说非常有利可图,但反驳的话,则可能代价高昂。 一旦你意识到无节制的市场不仅会带来金融危机,还会带来污染、气候危机、不平等危机、阿片类药物危机、美国儿童糖尿病危机等,你就会开始意识到这些无节制的市场确实存在问题。因此,你既要反对简单化的想法,也要反对金钱利益 。”
斯蒂格利茨表示自己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为什么米尔顿•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•哈耶克的观点是错误的,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他的新作《通往自由之路》中。他在这本书中再次呼吁建立“进步资本主义”,并主张,政府采用税收、支出和监管政策来控制企业力,减少不平等,并开发满足社会需求的资本。
因为分享会在爱丁堡举办,这让斯蒂格利茨自然而然联想到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、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•斯密。斯蒂格利茨表示,他的观点可能源于亚当•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。他说:“亚当•斯密认为‘看不见的手’、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’会通过‘看不见的人’带来社会的福祉。但亚当•斯密还要更聪明,他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,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监管。他认为这是一股创新的力量,但必须有法规来确保这股力量以正确的方式得以引导。”
---
早在10多年前,斯蒂格利茨就曾呼吁一些发展中国家征收环境污染税,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,并用税收的收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。斯蒂格利茨在讲座中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。他阐述: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存在很多污染,但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。在我有生之年的七、八十年间,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。例如,全球GDP增长了15倍。70年前,我们还没有达到地球的极限。今天,我们已经到达了。此外,10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担心温室气体,但不幸的是,我们并没有……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一点,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。但那么多人,尤其是美国的共和党人,他们要么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,要么说,反正我们什么也不会做。更深层次上,我在《通往自由之路》中试图提出的一个观点是: 在这里开始的启蒙运动如何让社会组织更合理化,让社会组织更了解世界。科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,而我们也需要去思考,如何去完善组织社会、政治和经济的方式。所有的人类机构都是有缺陷的,我们不能期待完美的政府或完美的市场 。”
“我们需要检测和制衡,但关键是,我们在许多领域需要集体行动和共同努力。通过共同努力,我们可以完成个人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我们需要约束:若不知道污染问题,我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,但现在我们需要了。如果你与世隔绝,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噪音,但我们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,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噪音污染……我们不得不要思考,我们如何权衡这些自由,以及我们如何扩大每个人的自由。”
斯蒂格利茨在分享会中探讨了分权经济和联合经营模式。他指出:“在这种分权经济中,有许多不同的单位,其中一些单位将以盈利为目的,比如一家钢铁公司,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机会,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创新,找出并制造出更好的产品。 但我们经济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护理经济,比如照顾老人。仔细想想,你是否希望对冲基金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?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因为如果你是对冲基金,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尽量给他们提供最少的服务。 对私营部门来说,监狱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领域。 囚犯对你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没有太多的选择。在美国,我们确实成功地对私营监狱的狱警进行了一些培训。他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审问和拷打方面尤其出色。因此,一些最优秀的刑讯人员就是在我们的私人监狱中培训出来的。好吧,你可以说,这也算是带来了一些社会效益(讽刺)。”
“有很大一部分经济不属于私营、营利部门,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制度模式,比如联合经营,我们很少谈论联合经营,实际上,联合经营在很多领域都非常成功。2008年金融危机中,美国最成功的银行是信用合作社,之后,它们也是唯一从事小企业贷款的组织。现在,我特别支持合作模式(Co-operative mode)。”
但市场本身并不擅长结构性的转型。斯蒂格利茨认为旧人因为利益,不会非常有效、非常顺利地转向新人的利益。因此,这就需要一些政府推动力,或者一些民间集体行动。他以美国铁锈带加里镇和曾经的“钢铁之都”匹兹堡的转型为例。
“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,加里镇不再生产钢铁,这里也没有工作机会。实际上,那里的钢铁产量和以前一样多,只是不再需要很多工人,因为他们的效率已经提高了很多……我去拍了一部关于全球化问题及其影响的纪录片。这里的一家钢铁厂被一家印度公司收购了。他们把它建成一个电影拍摄基地,并在这里拍了一部关于索马里战争的电影。在他们看来,加里看起来和索马里一样破败,但更安全一些。”
“让我再举一个钢铁城市的例子。匹兹堡已经完成转型,成为一个教育、研究和医疗中心。这要归功于政府,归功于卡内基梅隆大学,归功于宾夕法尼亚州对匹兹堡大学的支持。这座城市已经完全改变,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城市。而摆脱钢铁行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污染减轻,可以在这里自由呼吸……如今在匹兹堡,你可以看到星星。”
在分享会的尾声,有一位观众提问英国是不是必须存在占人口总数20%的底层贫困人群?斯蒂格利茨这样回答:“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不平等,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我们不需要你所说的那种极端的不平等: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,有20%的儿童在贫困中长大,而英国的数字也不相上下。我在我早期的一本书中,曾这样描述: 不平等是一种选择,但不是穷人的选择,而是我们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做出的选择。 拜登总统在‘疫情后恢复计划’中加入了一项条款,计划在一年内将儿童贫困率从20%降至10%左右。但共和党人随后认为,这个比例太低,他们现在提出废除这项计划,让儿童贫困率回到20%……在目前的竞选中,这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。令人欣慰的是,美国副总统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正提议将那些使儿童贫困率下降的计划永久化。”
有观众问斯蒂格利茨是否对这个糟糕的世界怀有希望?斯蒂格利茨说:“如果没有一点希望,我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。写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希望: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开始了解发生了什么,这场战斗就会以某种方式获得胜利。”
他继而补充,“市场会失灵,政府也会失灵,正如我之前所说,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。人类容易犯错,所有人类机构也都会犯错。”
文章编辑: q8ytop.com